
陈聿东——节气文化是中国人 自我认识的一个尺度(图)

陈聿东 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国际艺术交流协会主席、南开艺术校友会常务会长兼秘书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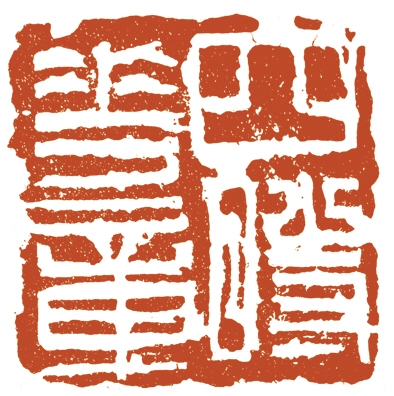
梁旭华 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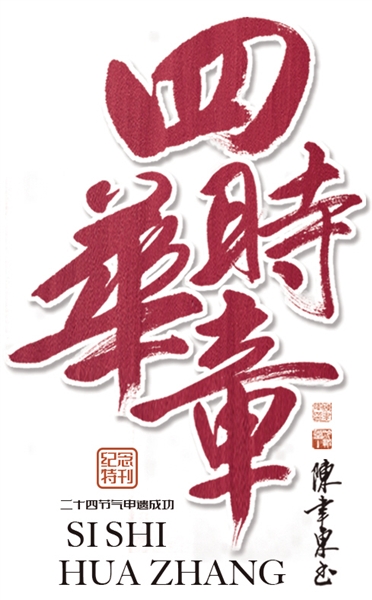

作为文化和旅游部非遗评审的专家组成员,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陈聿东一直致力于挖掘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包括二十四节气、昆曲等在内的东方文化瑰宝为世人所深刻认知,做出了很多努力。听闻本报推出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四周年纪念特刊,欣然题字“四时华章”。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陈聿东教授心中的二十四节气和东方文化。
新报:首先感谢陈聿东教授为本次特刊题字。您是文化和旅游部非遗评审的专家,曾参与了联合国非遗的一些培训和评审活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东方文化的传播。请您从非遗的角度谈谈对二十四节气的申遗背景。
陈聿东:首先要感谢每日新报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的不懈努力。我在哈佛大学期间,应邀出席过两次联合国的有关会议,一个是全球互联网方面的,一个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方面的。在国内,我又荣幸地被纳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审专家小组。随着人们文明意识、文明视界的不断开拓和延展,并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怀的进一步增强,对于人类的,包括我们祖先和现代人创造的各种文化产品的继承、发展、传播日益受到重视,各种组织机构不断健全完善,而联合国非遗评审组织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2016年11月30日,中国的二十四节气通过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列入名录,这是特别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新报:四年前听到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的消息,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陈聿东:能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然是非常荣耀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直以来,我们为评审工作的纯粹且规范化做着不懈努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资源和产品的逐渐丰富,人们对传统中精神层面的遗产进行重新判断和关注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逐渐发现和理解了传统文化潜在的“价值”。因此,近几十年来,有很多项目在进行逐级申报,很多地区、很多团体都在积极做这方面的工作。也必须承认,目前还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有的项目本身非常好,但申报材料准备得不充实不完善。到了国家级评审的时候,自然要严格把关,因为它代表着一个国家优秀文化的高端精华。所以,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了,具有特别重要的代表性和引领作用。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迄今有两千多年的发展传承历史,它涉及中华民族农耕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是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的时侯、气候、物候“三候”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节气的总结传承对指导农事的意义非常大。
新报:您不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专家,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家评审组成员,你怎么看待当下中国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
陈聿东:近期,我刚参加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审工作,我参与的艺术美术类就已有400项进入国家级的名录。怎样做才能使中国的非遗项目达到相关国际非遗组织的认同和支持呢?我认为,在申请前务必先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方针主旨和条款规则熟悉掌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文化遗产名录里面共包括五大类型,有口头语言文化类的,像西方的荷马史诗,咱们中国的格萨尔王史诗,都属于这一大类。还有舞蹈戏剧类,我国的昆曲在2001年已经进入了名录。像咱们的太极八卦、葫芦刻花、木雕、刺绣,都可以在了解掌握规则的前提下进行申报。有些项目还要进行深入挖掘,比如它的历史源头及相关的文化资源,要尽可能准备得充分一些。另外,项目目前有没有存在的基础,特别关键。有的项目传统有了,但存在的基础几乎“奄奄一息”,那就不太好被列入了。当地政府对申报项目的保护力度,社区群体和人员从事该项目的积极性,都是评审关注的重要方面。我们传承传统文化,不只是把它像老黄历那样供起来,要不断补充完善,在实践中展现活力、焕发活力。
新报:昆曲是世界非遗项目。据了解,您对昆曲非常有研究,同时还担任着南开大学甲子曲社的社长。昆曲和节气,看似好像不搭,实际上它们也有很多的关联性,您怎么看待昆曲艺术?
陈聿东:甲子曲社是北方研究、传播昆曲艺术和培养昆曲人才的重要社团组织,最早是由南开大学的一些昆曲爱好者(包括学者和教授)为继承传统文化、自娱自乐而组织的雅集活动,现在已经产生很大影响。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京剧、川剧、越剧等剧种都受到过它的影响。昆曲里面容纳了诗词、音乐、舞蹈,题材大多表现才子佳人,自然也会表现书法和绘画门类(过去的才子佳人都要擅长一点书画艺术),也包括唯美的艺术舞台设计、服装道具等,所以它是综合性的艺术表演形态。另外,中国现在的制造业也较为发达,昆曲所需的服装、道具、布景,再加上灯光音响的“声光电”效应,调动起来都比以前容易了许多,因此更有助于增强这一高雅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感染力,观众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能够充分领悟和感受到昆曲之美,提升欣赏品位。现在的文化传播条件也非常便利,走出国门的机会也多了,把中华传统文化向世界去介绍和推广,与其他文明平等对话,相互欣赏借鉴,我觉得当下是很好的时机。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昆曲艺术走向更广大的空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新报:节气文化与昆曲的表演能否有机结合?
陈聿东:戏剧情节里面,节气文化的符号俯拾皆是,譬如《西厢记》里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不着痕迹地呈现气候、物候及景象,戏曲人物出行、赶考、农耕、收获……都会有节气元素。不光是气候、时候和物候,节气文化深深浸润在中华更宏阔文化场域当中,如果没有节气,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种诗意的境界恐怕就不容易渲染出来,还有《千字文》的“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诗经》里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等等,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节气文化影响着中国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把它抽离出去,那么很多文化的“骨架”就会松垮和缺失,因为节气文化是一个维度,可以说是界定我们人类存在的自我认识的一个尺度。二十四节气把我们的时空观、美学观、文学观都有机融合在一起,是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一个特性,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众多源头之一,它会一直激励我们中国人为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遗产而承担起我们应有的责任,并为其弘扬光大而不懈努力。
新报记者:张治
来源:天津文学艺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