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骥才最新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近日出版(组图)
冯骥才重续文学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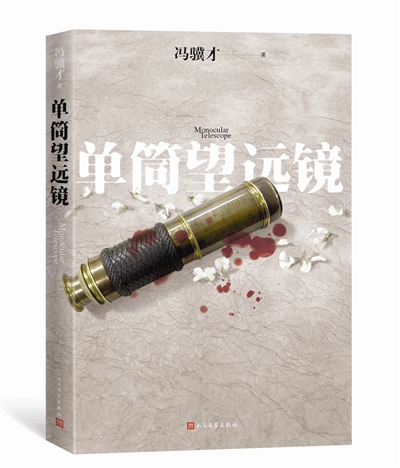

完成《单筒望远镜》书稿后,冯骥才自拍一张。

改稿子,冯骥才写秃了一大堆铅笔。
冯骥才最新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部近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是冯骥才继《神鞭》《三寸金莲》后,又一部反映天津地域文化的虚构性文学作品。三十年的沉淀,使这部作品呈现穿越历史文化时空的厚重面貌,也书写了冯骥才对历史人性的透彻思考。
在中西最初接触之时,彼此文化的陌生、误读、猜疑、隔阂乃至冲突都在所难免;而在殖民时代,曾恶性地夸张了它,甚至将其化为悲剧。
历史存在的意义是不断把它拿来重新洞悉一番,从中获得一点未来所需的文明的启示。
当代人写历史小说,无非是先还原为一个历史躯壳,再装进昔时真实的血肉、现在的视角,以及写作人的灵魂。 ——冯骥才
《单筒望远镜》封底印了冯骥才这样一段直白、深刻的文字,诠释了他对这部作品的夫子之道。
从未离开文学,终于“重返小说”
在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激流中,冯骥才既是整个新时期文学发展变化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这个时期文坛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活动家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冯骥才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进行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的保护,但他一直没有离开文学领域。从文学的凌汛期到新时期文学开创,再到投入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与文化遗产保护中,冯骥才先生从不是文学的旁观者,也始终没有离开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立场。
2018年,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足本)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再一次获得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领域的最高奖项,这不是冯骥才第一次在小说界折桂,他的《雕花烟斗》《啊!》《神鞭》都曾获得鲁奖的前身——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
肚子里“放了”很多小说和人物
虽然投身文化遗产保护二十多年来,冯骥才很少再写小说,但包括《单筒望远镜》在内,其实他在肚子里“放了”很多小说和人物。他经常在奔赴田野考察的路上,把肚子里的小说“掏出来”过瘾。一路上,他会想出好多特别有趣的细节、特别精彩的故事。然而司机师傅一声提醒“咱们到了”,就好像从梦里突然醒来,一切烟消云散,再也回想不起来。但正是在这样不断想象的过程中,小说里的人在冯骥才心里活了起来,变成他认识的人。
冯骥才说:“写小说的时间不一定要太长,但放得时间一定要长。时间长,人物才能活起来。小说的写作过程靠灵感爆发,当人物活起来的时候,这个人物你是摆弄不了的,人物一定要牵着你的鼻子走,小说才能写得有意思。”
50天完成初稿
动笔开写《单筒望远镜》,冯骥才记得很清楚,是去年9月18日。那天上午,他在张掖开非虚构文学研讨会,做完一场演讲,有点疲劳,还有点高原反应。下午,年轻人都跑去马蹄寺玩儿,他就留在旅馆里休息,靠在床头上,小说的开头忽然冒了出来,他拿起手边的iPad一口气写了一千多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只用短短50天便把初稿写完。但他习惯一部作品改七遍,《单筒望远镜》下印厂前,他又加了1万字,让小说的细节更丰满。
从当年写《义和拳》的时候起,冯骥才先生就对义和团和天津租界区的历史资料非常感兴趣,不仅搜集了一切他能搜集到的文字史料,还搜集了不少当年的实物。例如此次小说里用作插图的年画,结尾处照片里那支长筒手枪,以及小说最关键的意象——单筒望远镜。
《单筒望远镜》虽然不足15万字,但特别厚重,特别有味道。“单筒望远镜”出现在上世纪初或者上上世纪末,当代很多人没用过或者也没玩过,甚至没见过真的东西,或者只是在博物馆见过。电影中,有过洋老头、洋老太拿着一支单筒望远镜的镜头:一个单向的联系,一个互相窥视的状态。《单筒望远镜》抓住了这样一个意象——充满了味道的意象,充满了象征意味的意象,因此作品就从这里进入了。
《单筒望远镜》描述了一个纸店的老板欧阳先生的两个孩子,一个欧阳尊,一个欧阳觉,在中西文化发生碰碰的特殊环境下的命运。一段跨国恋情,沉醉于悲怆的历史河流中。古朴精致的语言,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一百多年前的天津风貌和中西冲撞的惨烈跃然纸上。单筒望远镜成为文化对视的绝妙象征:世界是单向的,文化是放大的,现实就在眼前,却遥远得不可思议。
“单筒望远镜”:世界是单向的,文化是放大的
十九世纪,天津是东西方最早冲突的地方之一。1862年之后天津建英、法租界,外国人进来后,开始和中国人有最早的接触。在这片土地上,东西方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的交流和冲突越来越多。而天津又是一个特别的地域,作为商业城市比较洋气,作为一个码头又五方杂处,充满地方民情和自己的特点。对于那段时期的材料,冯骥才看得非常多,从《义和拳》到《神灯前传》,他一直试图通过挖掘历史来反思民族心理文化。
《单筒望远镜》起源于冯骥才对上个世纪初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思,也延续了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在那个时代,世界的联系是单向的、不可理解的,就像隔着单筒望远镜一般,彼此窥探,却又充满距离感。“正如男人眼中的女人,不是女人眼中的女人;女人眼中的男人,也不是男人眼中的男人。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人,不是西方人眼中的西方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人。”那个时候的世界没有沟通,中西方相互不理解。在最早的中西冲突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悲剧式的问题,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主义,也有文化的冲突。《单筒望远镜》则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写在了里面。
在中西文化冲突最激烈的时刻,爱情能否超越国界?在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中,灾难因何而起?这样的文化景观下,人性会遭遇怎样的炼试?《单筒望远镜》以一段跨文化的恋情坠入历史灾难的故事,抒写一百多年前普通人所经历的灵魂深处的痛苦,探究中西文化沟通的困局,探寻人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边界。
《单筒望远镜》延续了冯骥才独特的语言风格和精湛品质,也尽显他描摹生活的扎实功底,小说以独特的津味儿,将斑驳的历史再次拉入人们的记忆中,还原一百多年前天津人、普通民众的精神性格,在种种社会矛盾下,在小人物的爱恨情仇与心灵历程中,演绎着中西文化历史碰撞下的时代悲剧与命运悲剧。
重启意象型小说 再续“怪世奇谈”
《单筒望远镜》是继《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的“怪世奇谈”四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酝酿时间最长的一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单筒望远镜》的写作计划已频繁出现在冯骥才的各种访谈中,由于他被卷入文化遗产保护的“漩涡”,这部书的写作也被搁置。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沉淀,《单筒望远镜》终于在漩涡之后以更成熟的面貌浮出水面。
《神鞭》通过一根辫子反省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三寸金莲》针砭了中国封建文化的顽固性及其束缚力,《阴阳八卦》剖析思辨了中国文化的认知方式及其负面,《单筒望远镜》则从中西文化碰撞的冷峻现实中,揭示了因为接触障碍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双方彼此认知都产生了许多错觉。单筒望远镜,是莎娜和欧阳觉彼此提供给对方的一个窗口,未知带来的激情将他们双方引向一条单向路,在他们的背后是中西双方单向认知带来的隔阂、误读、冲突,而炮火最终碾轧了一切,爱情也毁灭在那个悲剧时代。
文学里意象也很重要,比如《神鞭》,“我们历史是很伟大的,我借助辫子,辫子是一个意象,是伟大的、无往不胜的,但是在新的时代里这个辫子又有问题,我借了这个意象。我写《三寸金莲》小脚,不是写那个人的脚,实际是写束缚,我们的文化里有一种自我束缚力。小说我都用了意象手法,比如我写的小白楼,我写的古槐,盘根错节的古槐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意象,天津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冯骥才说。
把文学变成艺术品
冯骥才是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作为画家,无论是景象的画面感还是形象的画面感,冯骥才都特别注意。冯骥才表示,特别喜欢契诃夫,契诃夫喜欢画画,他的小说里面画面感很强。普希金的画面感也很强,“我写过一篇文章,俄罗斯的作家大部分都愿意画画,陀思妥耶夫斯基画画,普希金画画,托尔斯泰画画。我喜欢把文学变成一个艺术品。中国还有特别好的工具——就是文字。从我们的文学史来讲,我们的诗歌成熟在前,散文成熟在后,诗歌影响散文,所以中国的唐宋八家的散文都像非常精美的艺术品”。
对于人物,冯骥才在小说《单筒望远镜》里有意识写两个女主人公,一个是受儒家影响的,自我约束的,但是一个娴静、优美的中国文化养育下的女人,像中国古代知性的女子。还有一个是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一个自由的,又开放的,纯真的女子。让这两个女子交集在主人公的命运里面、心灵里面折磨他,“折磨他,就是为了让读者思考”。冯骥才不喜欢悲剧,“可是小说没办法,有的时候悲剧有悲剧的力量”。冯骥才喜欢悲剧之后给人留下很多情感的或思考性的东西。
今年76岁的冯骥才坦言,让他跋山涉水比较困难,但是该做的工作必须做。现在返回文坛,在书斋的时间多一点,返回文坛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热爱文学,“我心里实在有东西要写。不是我要写小说,而是我有小说要写。我还会为文学努力,为文学效力”。
来源:天津文学艺术网

